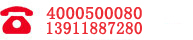各地房價是漲是跌尚在未定之天,但有一個地方卻已初見分曉,那個地方不是溫州,不是鄂爾多斯,不是榆林,而是沿海各地,北起渤海灣的大連、營口、秦皇島,到膠東半島的煙臺、威海、青島,再到南方的惠州、三亞、北海,都進入“海景房泡沫”破滅的前夜。
多年來為地產(chǎn)商們追逐的海岸線,遍布密密麻麻的住宅樓,曾經(jīng)吸引著全國各地的人爭先恐后,買下一套或者數(shù)套一年也住不上幾天的海景房。如今這些動輒幾千上萬畝的大項目,夜幕降臨時,只有一片沒有燈光的建筑物,形如“鬼城”。當(dāng)年熱得燙手搶也搶不到的海景房,現(xiàn)在打折出售也是“有價無市”,威海銀灘一帶,2008年購入價50多萬元的房子,現(xiàn)在出價20萬元也乏人問津,“爛在手里”是許多購房人的共同絕望。
業(yè)內(nèi)人士概括中國的海岸線開發(fā)亂象時,往往會指出三點原因:一是開發(fā)時機不對,過早透支了海岸線資源;第二是缺乏好的規(guī)劃,開發(fā)商一哄而上,造成了破壞性開發(fā);第三是沒有一個核心產(chǎn)業(yè)支撐,沒有健康的經(jīng)濟生態(tài)鏈,無法持續(xù)發(fā)展。也有計劃,也有審批,但最后結(jié)果仍然是毀壞了寶貴的海岸生態(tài),卻沒有建成預(yù)期的“旅游度假勝地”,只有成片水泥鋼筋森林,在靜謐的夜間憑借著幾盞孤燈,形影相吊。
海岸線開發(fā)如何不合理,海景房泡沫有多大,不是這里關(guān)心的,值得探究的是,中國過去奉行“計劃經(jīng)濟”,改革開放之后,政府仍牢牢抓著行政審批不放,既有發(fā)改委,又有證監(jiān)會,不要說重大項目必須批準(zhǔn),連一家小小企業(yè)上市也需要反復(fù)過堂才得以放行。據(jù)說這樣才能確保經(jīng)濟發(fā)展的協(xié)調(diào)有序,其實無非換湯不換藥的“計劃”思路。
一切“計劃”思路無非出于同一個信念,那就是政府一家做主,而不是由著市場主體自主,可以保證更高水準(zhǔn)的整體合理性,所謂“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可是無論海岸線開發(fā)的亂象,還是企業(yè)上市中成長性超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遠走海外,而虛假包裝的猖獗于國內(nèi),都證明最講“計劃”的政府最后帶來的結(jié)果卻是最沒有計劃的混亂。這又是什么道理?
說得大一點兒,所有相信政府可以實現(xiàn)最高合理性的人士,都是對人類理性的過度迷信者,總認為一小撥精英的思考能最好地實現(xiàn)合理的效果。哪知道哲學(xué)家早就證明,以人類理性之有限,與其將決定權(quán)交給一部分人——縱然他們夠得上“精英”的稱呼,也不如讓所有個人自主決策,然后通過相互競爭,實現(xiàn)資源最有效的配置。
說得小一點兒,所有迷信計劃的人士同時也是相信政府能夠完全出于公心,從長遠的公共福祉用計劃的方式落實下來,而不會像市場主體那樣每人只從私利出發(fā),不關(guān)心公共利益。可如今誰都知道,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利益群體,各個部門也是大小不等的利益群體,所以政府決策同普通市場主體基于私利做出的決策,沒有本質(zhì)上的差別。在短期任期制的刺激下,官員要么抓緊出政績,然后升遷,要么乏善可陳,眼睜睜看著下屬變成上司。“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路易十四的至理名言折服了多少官員,抓住眼前機會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最高策略。
所以,大自然多少年才能形成的海岸生態(tài)與我無關(guān),多少漁民、農(nóng)民、市民需要這條產(chǎn)業(yè)鏈與我無關(guān),新興旅游度假區(qū)需要怎樣的整體開發(fā)和連續(xù)推進與我無關(guān),甚至購房者包括投機者買了海景房還能看到多少值得一看的海景,以便將來脫手給接盤者都與我無關(guān),唯一有關(guān)的是任期內(nèi)海岸線和海景房能營造出多少政績,如果不算尋租機會的話:當(dāng)一個以公共利益承擔(dān)者自詡的政府實際上是由千千萬萬個自利的個人或集團所組成的時候,無論精英,還是理性,還是計劃,都是靠不住的,比普通市場主體更靠不住,因為有強制性行政權(quán)力的介入,其一意孤行是完全失控的。海岸線上的“海景房泡沫”證明了這一點,除了個別線路之外,幾乎全網(wǎng)虧損的高鐵證明了這一點,全世界最高水平的M2也證明了這一點,2013年以來被查處的“老虎”“蒼蠅”更證明了這一點。
放在這個背景下,再去理解李克強總理所謂“凡是市場或社會能辦的,就交給市場或社會來辦”和國務(wù)院強力推動的取消行政審批事項,就不難明白其中的深意。政府和計劃如同人類理性一樣,是不完善的和有缺陷的,等待著無數(shù)個人的自發(fā)行動去彌補和糾錯。
更多資訊閱讀請關(guān)注北京辦公裝修東方華美